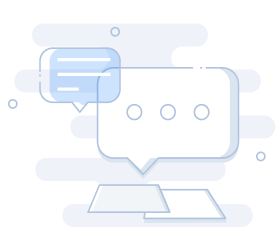流浪的老兵达琳·马修斯在自己的车中度过了超过两年,等待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的住所票券。她于1976年参军,被送往阿拉巴马州麦克莱伦堡。“我当时准备参加都是女兵的军队,觉得这样就没有了性侵害的问题,但是我参加了,性侵害的问题还是存在,”马修斯说。

露瑞·豪斯19岁的时候是B29轰炸机的技工,遭到空军中队一名男子强奸。她从没举报过这件事。

黛布拉·菲尔特1978年参军,在毕业聚会上,她和数名女性遭到强奸。

梅利莎·A·拉莫在空军呆了9年,称在那里的训练官和男空军人员手下经历了持续的性心理创伤。

“你看到条纹,认为那是权力和权威。我接受了,因为如果我不接受,影响的是我的事业。我有规则,而他没有。无论他怎么看待它,他的话都和我不同,”梅利莎·拉莫在谈到训练官时说。

梅利莎搬进一家叫做“丛林”的汽车旅馆。她说,这样的处所通常不允许12岁以上的男孩居住,所以她和13岁的儿子从一处旅馆搬到洛杉矶外的另一处旅馆。

梅利莎经历了军队性侵害的心理创伤,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,不得不向多家非政府机构求助。

梅利莎尝试为儿子系领带,准备他的8年级毕业典礼。

梅利莎亲吻儿子山姆。

前海军队员萨拉·詹金斯接受救济。

克伦·史考特1985年参军,成为了性侵害的目标,之后的7年被强奸7次,面临持续的威胁。

桑德拉·薛尔曼只在军队呆了几周就称,曾在一个派对上被强奸。

格兰迪·戈尔登称,她参军是想要逃离性虐待的家庭生活,但在18个月的服役期间,被性侵害了7次。

空军退伍老兵玛格丽特·布鲁索-索亚,曾在新兵训练营中受到过训练官残忍的性侵害。

威尔玛·M·赫恩登嫁给了一名士兵,后来遭到他的殴打和性侵。

迪得莉·D·罗奇在高中之后参军,开始很享受。当她开始争取第一次的晋升后,她说发现自己不得不“做更多的事”。

当保拉·安德森告诉她的军团指挥,她被一个士兵注射毒品并被强奸之后,她就被遣送到了韩国。在监狱中呆了17个月之后,自2015年2月开始,她就无家可归。

晚上,保拉·安德森睡在停在一个教堂停车场的汽车里。“军队教给我们如何在大街上生存,”她说。“他们教给我们如何在不同的气候环境中宿营和生存。”她说她的部队生涯持续了6年,但是她的军队性侵创伤20年来都没有离开过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