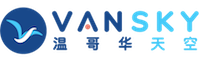错误
我打江南走过,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。
细雨湿衣。江南依旧是一片氤氲,三月的风撩起岁月无痕在小桥流水的人间安家落户。春雨初霁,积水顺着瓦楞从檐间滴落,叮咚叮咚,错落有致。
闲花落地。朱阁半启,玉儿停坐在窗前,望着窗外花开花落,云卷云舒,一双眼眸清澈无痕,澄滢如水。花飞花谢,到而今春秋又一载,然归人何处是?
楼梯上传来“咚”、“咚”的声音,缓慢而沉重。玉儿回身去开门,门外站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。男人髯须浓密,依旧穿着前朝的长袍,手中拿着一个烟斗,见了玉儿,迟疑了一下,道:“玉儿,你怎不做绣?”
玉儿转过身,回到妆前,对镜子理了理头发,问:“爹,承义哥哥甚么时候回来?他不是说今年春天回来看我的吗?”男人进屋,坐在一张凳前,抽了一口烟,呛得咳嗽了起来,咳过了,道:“玉儿,河西的赵二家爹去了,那孩子也还实诚,你若同意,选个日子就嫁了吧!”
玉儿不说话,继续弄着头发,纯黑的发丝垂下来,是一种流动的美。男人又道:“现在的世道,找个好人不容易,衙门天天抓人,留你一个女儿在家里,总不太安全。”
玉儿停了停,将宝奁饰物全解下来放在妆台上,许久,才道:“爹,不是衙门,清朝不在了,现在都是民国六年了。”
“哦……”男人叹了一声,眼神有些迷离,忽而叹道:“你说那些学生好好的书不念,干么革甚么命,听说昨天晚上又抓了两个,还有承……”男人忽然停住,低头又开始吸烟。
一吸烟,又开始咳嗽,男人眉头皱了皱,重重的叹了一声,望着天外,渐渐出神。三月的风蹑手蹑脚的藏头露尾,时而扬起片片飞花,随风翻逐。
“爹,承义哥哥……他是不是出事了?”玉儿忽然问道。男人一怔,回过神来,看着玉儿,问:“玉儿,你怎会如此说话?”玉儿道:“街上到处都贴着呢!爹,他们说承义哥哥是革命党,革命党是做什么的?承义哥哥干么要做革命党?”
男人忽然站起来,峻声问:“玉儿,你上街了?我不是不让你去吗?你上街作甚?”玉儿忽然觉得委屈,只低头道:“爹,承义哥哥,他还会回来吗?”男人也终于沉默,轻轻地摇摇头。细雨又起,街道上行色匆匆。丝雨无边,也无法羁绊行人的脚步;闲花落地,亦无法挽留世道的变迁。革命,革命……真的有这个必要吗?承义,你的牺牲,就真的值吗?
“爹,我嫁。”玉儿忽然道。男人心中一震,却是怎么也高兴不起来,望着女儿无奈的应允,男人不由痴笑一声,此生浊浊世道,该如何换得朗朗乾坤?
街上,一对夫妇漫不经心地谈论着今天政府杀害的两个学生,也许,这只是他们茶余饭后的话柄,日久,便会随风散了罢?
乱雨无边,点缀着寂寥的心事。空怅天涯,花已岑岑寂。
我打江南走过,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,如莲花的落。